關鍵詞 |
字畫私人收購,書法字畫收購,張大千的字畫收購,名人的字畫收藏 |
面向地區 |
一件元人書畫,一人看為假,旁人說它真,還不要緊,至少表現說假者眼光高,要求嚴。如一人說真,旁人說假,則顯得說真者眼力弱,水平低,常致大吵一番。如屬真理所在的大問題,或有真憑實據的寶貝,即爭一番,甚至像卞和抱玉刖足,也算值得,否則誰又愿生此氣。
有一件舊仿褚遂良體寫的大字 《陰符經》,有一位我們尊敬的老前輩從書法藝術上特別喜愛它。有人指出書藝雖高但未必果然出于褚手。老先生反問:"你說是誰寫的呢?誰能寫到這個樣子呢?"這個問題答不出,這件的書寫權便判給了褚遂良。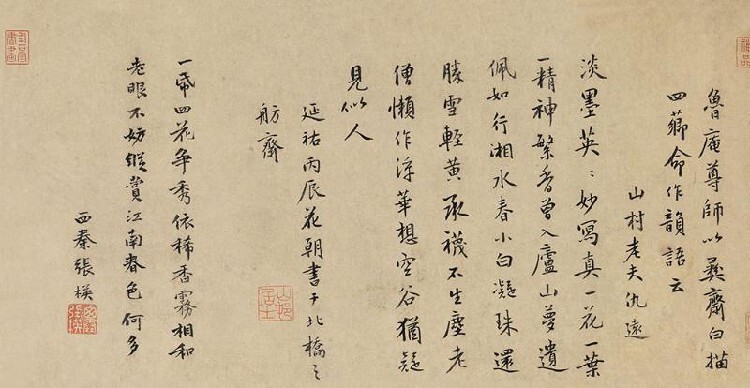
在楊新的學術之路上,徐邦達、啟功兩位先生有著重要的影響。
對于啟功,人們一般都知道他是書畫,其實他成名很早,而且與故宮有很深的緣分。民國時期,故宮博物院設有以學術活動為主旨的,所聘委員俱為有關研究領域的一時之選,故宮聚集了一大批中國當時為的文史及古物研究的學者。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故宮重建,后公布的47位委員中,有書畫10位,時年35歲的啟功就嶄露頭角,為世所重,與張珩、蔣縠孫、朱家濟、鄧以蟄、張爰、張伯駒、徐悲鴻、沈尹默、吳湖帆等并列;其他九位的專長都注明為“書畫”,唯啟功注明是“書畫史料”。楊新得到啟功指點,自是十分幸運。在楊新的書畫鑒定文章中,可以看到經常引用啟功的話。可稱為他代表作的《書畫鑒定三感》,不僅說明是受啟功先生《書畫鑒定三議》寫法的啟發,且其第二點“望氣”之法得失有無、第三點書畫鑒定的“模糊性”,就是直接引自啟功的論點并在此基礎上結合自己的體會作進一步闡發的。
楊新曾擔任徐邦達先生工作助手6年之久,受徐先生教導尤多,影響更深。
清宮舊藏以書畫銅瓷為大宗,15萬件書畫也成為今天故宮博物院的藏品優勢。從20世紀50-60年代,直至80年代,北京故宮所藏古書畫先后經過徐邦達、張珩、啟功等先生的鑒定,對這些書畫的作者、流派、時代、內容等方面給予了客觀的基本定位。其中徐邦達先生貢獻尤多。楊新從徐邦達身上受到兩方面教育:
一是學習徐先生對工作全身心投入的精神。楊新從徐邦達為故宮古書畫藏品所建的檔案資料中,深刻感受到先生的認真、嚴謹、細致:“在所立欄目中,除了登記其質地、尺寸、款字、來源等各項之外,還要對其收藏印鑒、題跋進行識別,對其內容、真偽、藝術等寫出評語,查出文獻的記載,后還有識真偽的結論等,實際是一次科研活動。先生所做的這些工作,為北京故宮博物院在書畫方面的陳列研究、編輯出版及對外交流等,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這些檔案至今仍然在使用。”(楊新:《我跟徐邦達先生學鑒定》)
《富春山居圖》 元 黃公望 局部
題跋,雖然它也是依據之一,不過,凡是書畫上并不都有,它不能如印章一樣可以左右逢源地隨時運用。題跋本身是書,而取以作證的在于它的文字內容,這些文字的內容,或者以詩歌來詠嘆書畫,或者以散文來評論書畫,或者記述書畫作者,或者評論前人的題跋的當否并對書畫加以新的評價,它對鑒別也具有很大的說服力。
《搗練圖》 唐 張萱 宋摹本 局部
年月:書畫上或題跋上所題的年月或與作者的年齡、生卒年不符,或與事實有出入,也將被認為是作偽的佐證。
避諱:在封建帝王時代,臨文要避諱,就是當寫到與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寫一筆,這就叫避諱,通稱為缺筆。在書畫上面,看到缺筆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諱,就可斷定書畫的創作時期,不能早于避諱的那代皇帝的時期,否則就是作偽的漏洞。這一問題,一向作為無可置辯的鐵證。
題款:以書畫的題款作為鑒別的主要依據,只要認為題款是真,可以推翻其他證據來論定真偽。
如從以上方面對一幅古書畫進行鑒定,即使不確定該作者的筆墨特征,也能從容自信面對 。
印章作為鑒定書畫的一個主要方面,是重視的,因為對于中國書畫來說,大多都是有印的。如果一幅標明清中期作品上的印章與已知的確為真跡上的印章完全一致,其他方面又無疑問,基本上就可以斷定為真跡。因為在一般情況下,臨摹復制的印章多少都會與原印有所不同,印章是極難仿制得與原印一模一樣的。
